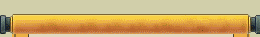律诗、永明体及其他
◆吴忱
尝读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见其评张九龄《望月怀远》云:“律诗本来是要讲对偶的,这诗的颔联,在字面上看,似乎对得不甚工切。不过我们要知道初唐时期律诗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时未免还留存着古诗的格调。”诗如下: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张九龄当初盛之际,诗主清澹,无六朝靡缛之习。此作前半截意到笔随,一片神行,颔联虽不免以虚对实,然确是律体。
不过喻氏所指的情况确实存在,却举错了例子。唐初承六朝永明体余绪并加以变革,律诗基本体式随之确立,已臻完美,诗坛从之者蜂拥群起,历千百年而遵之勿失。但唐人去六朝未远,仍不免受旧时代惯性制约,故尚多貌似近体而实则永明体之作,晚近文学史论者但看局部俳偶,而不解整体粘对,多有误指误举者。胡应麟《诗薮》曰:“若唐初句格未谐者,自是六朝体。”绝不可不加甄别。
譬如王勃,《全唐诗》录诗九十余首,其中五言四韵三十首,合五律句格者仅有八首,余皆为六朝体。有句脚三平调者,如《散关晨度》之“石路无尘埃”;有句中四连平者,如《寻道观》之“芝廛光分夜”。更有失粘失对者,如《麻平晚行》:
百年怀土望,千里倦游情。高低寻戍道,远近听泉声。涧叶才分色,山花不辨名。羁心何处尽,风急暮猿清。
及《铜雀妓》:
妾本深宫妓,曾城闭九重。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前作一二两联失于粘缀;后作三四两联除“锦衾”句与前半首平仄失粘外,“罗衣”句又平仄当联失对。
可知王勃绝大部分诗作尚未脱齐梁旧习,因此律诗之“没有完全成熟”,当指此类作品而言。而律诗粘对体式的确立,正如郭绍虞《从永明体到律体》所说,“是由永明体到律体的一个重要关键”。
王勃之作大抵如是,而陆侃如《中国诗史》说:“在四杰集中,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格律之严与数量之多,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础。”显然将不合律体句格的永明体都一概算计在内了(如该书误举多首失粘之作,称“七绝七律到此已成熟”云云),事实上,王勃五言律体尚不及全部诗作十分之一。他如卢照邻诗一百余首,其中五言四韵二十五首,合五律句格者止有六首;骆宾王一百三十余首中,五言六十三首,合律之作亦仅二十二首;惟杨炯虽仅三十三首,而五言十五首均为合作。一燕不成春,所谓“格律之严与数量之多”,所谓“奠定基础”,从何说起。
前于四杰,王绩亦初唐诗坛之佼佼者。杨升庵称其“诗律”为四杰之“滥觞”、沈宋之“先鞭”。据《王无功文集》所收四十首五言四韵之作中,五律亦有十四首,固难能可贵。因“不乐在朝”,“才高位下”,一生波澜不惊,但有诗名而已。
大凡一种新体之起,必有大力者为之推助,或以其作品示范,或以其地位号召。而王杨卢骆位不逾县令,合律之作数不过半百,且除杨炯外均未尝倾力为之。纵有开启之功,位卑言轻,未必已成气候。登高一呼,尚有所待。
考初唐律诗之成熟,实自沈宋大量制作开始。中宗时两人均拜修文馆直学士。沈佺期,《全唐诗》录其诗一百五十余首,除古体外,五律六十五首,七律十四首,排律三十首,绝句八首。宋之问,共有诗一百九十余首,而五律七十九首,七律三首,排律三十一首,绝句十八首;其余则古体。此外永明体亦各有十首,这在转型时期自属不免;但两人五言四韵之作纯系律体,不沾六朝余沥一滴,而总量之多,诚可谓全力以赴了。
《唐诗纪事》录宋之问《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五排之作,云:“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退,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鶱举。沈乃伏,不敢复争。”观其场面,是两人皆居庙堂之高,其号召之力可知。
沈宋既有大量成熟作品示人以范,法度遂明,天下景从。《诗薮》曰:“五言律体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沈宋苏李,合轨于前;王孟高岑,并驰于后。新制迭出,古体攸分。实词章改革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
所谓“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靡缛”或指六朝余风,“拗涩”乃言其拗字涩调。可知胡氏对四杰的基本评价。
“苏李”即苏味道与李峤,两人年岁较沈宋、王杨略长,而皆勠力于律体。苏味道当武后临朝之际,前后居相位数载,所作《上元》诗有“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之句,脍炙人口。《全唐诗》仅收十六首,其中五律、五排、七律共十一首。李峤在中宗朝拜封赵国公,五律有一百四十八首之多,七律亦有三篇。此外永明体仍有十三四首。诗以五言咏物居多,但尚典丽,虽不容没其劳绩,而开山之功自不得不让于沈宋。
沈宋之前,杜审言亦近体诗史不可忽略者。《全唐诗》录其四十三首,即古体二首,五律二十七首,排律六首,七律二首,七绝三首;又永明体五七言、五排各一首。而《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律法之森严,为《唐诗三百首详析》标作范式。《诗薮》谓初盛间“五言律杜审言为冠。七言律沈佺期为冠。排律宋之问为冠”,甚至说初唐五言律以“独有宦游人”第一,洵非过誉。
继踵而起者,如曾拜修文馆学士的李乂,存诗四十三首,已全是近体,无一出律之作,苏颋称其“五言之妙,一变乎时,流便清婉,经纶密致”。苏颋年辈稍后,所作七十五首律绝亦仅有二三首失律。可见当时诗坛之一斑。
以上数人生虽并世,而沈宋之成绩与作用最称卓著。其出入禁垣,影响风气,四杰不能及也。因此,说五律之形成与普及是以沈宋为代表的宫廷诗人大力提倡实践的结果,或更合乎历史本相。
至“五言律体兆自梁陈”之说,《诗薮》列举陈后主、张正见、沈炯、江总,隋代何处士及北周庾信等人所作之合“唐律”者共十六首。此外漏网之作,笔者亦续得十首,如徐陵《关山月》: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思妇”一联虽未对仗,然已启王维“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常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等作方便之门。他如庾信《咏画屏风》:
今朝好风日,园苑足芳菲。竹动蝉争散,莲摇鱼暂飞。面红新着酒,风晚细吹衣。跂石多时望,莲船始复归。
则无一字不合。然而沈约等人虽倡导四声八病之说,但六朝绝大部分作品只注重个体而忽视整体,即注重上下句词性俪偶与平仄对立,却不要求前后联彼此粘缀,即节奏点上平仄相同。粘则谐,不粘则不谐,整体之粘缀与否正是近体与永明体脱钩的关捩所在。此犹投射于镜之物体与所反射之映像,譬若五律前半首是投像,后半首则其映像,粘者是镜中人,具对称性,对称则谐;不粘者是眼中人,不具对称性,不对称则不谐。正由于初唐诗人通过永明体的涵泳,发现粘缀具有对称之美、和谐之美,于是,便“发明”了律诗。
但永明体并非五言八句一种形式,更多是十句、十二句甚至数十句的长篇制作,至唐初则演化为排律。
王力《汉语诗律学》称庾信《奉和山池诗》“已经很像排律”,谢灵运“有些诗也已经和排律相类”。所谓“相类”,只如《艺苑卮言》所说“于古调中出俳偶”而已;且录庾信《奉和山池诗》如下:
乐官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限,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
此诗第二联失粘,第三联失粘又失对。永明体大率如此。
《诗薮》则曰:“薛道衡《昔昔盐》等篇,大是唐人排律,时有失粘耳。孔德绍《洪水》一章,则字句无不合矣。”《昔昔盐》因“空梁落燕泥”之句,历来传诵;只是胡应麟看走了眼,《洪水》也“时有失粘”。但同卷复又举阴铿《安乐宫》:
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鹍仰,联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雕梁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
而评曰:“气象庄严,格调鸿整。平头上尾,八病咸除;切响浮声,五音并协。实百代近体之祖。”读之洵然,王力或不免漏眼。
陈仅尝论及律诗源流,其《竹林答问》第二十问曰:“古诗之转为律,休文一人之力何能为之,抑别有说欤?”答曰:“休文何能为力!夫古诗之不能不为唐律,此声音之自然,即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故魏晋之音调异于两汉,宋齐之音调异于魏晋,自梁以降至陈隋,则名虽古诗,已全律体,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并举《文选》中曹植、刘琨、陆机、鲍照、颜延之、谢灵运、谢惠连等十数人“两句精工,平仄谐畅,全是律偶者”七十余联,论曰:“以上诸句,已纯乎律体,不必隐侯之‘命师诛后服,授律援前禽。函轘方解带,嶤武稍披襟’、‘唼流牵弱藻,敛翮带清霜’等句为唐贤启先轨也。”
此论似是而犹未的。譬诸行军,前于齐梁者,如曹刘鲍谢辈于古调中出以俳偶,一联或合,而罕有全篇,犹是散兵游勇,安能“为唐贤启先轨”?齐梁而后,采偶句、调平仄,长篇短制,此倡彼酬,“名虽古诗,已全律体”;然偶句固必备之条件,却并非决定之要件,若一联内上下句对位平仄混同,一篇中前后联对位平仄失粘,犹散兵游勇虽经收编而仍各自为营,依然不是律诗。必待其人之出而整肃军容、严明军纪、集中指挥而后可。迨至唐初,就齐梁永明诗法排比整饬,统一范式,而粘对之法亦应运而生。律法既明,则长篇演为排律,短句演为律诗,四韵俱成,八音齐奏,正如“临淮王用郭汾阳部曲,一经号令,气色益精明”矣。
自兹而还,五七言近体之法既定于一尊,其法之严固前古未有,亦不无“束缚思想”之嫌。据《唐诗三百首详析》所评,即使在近体盛行之后,出律之作仍时有所见。兹引喻氏之评及者如下:
如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评曰:“律诗颔联总要对偶,现在‘倚杖’虽可对‘临风’,但‘柴门外’决不可对‘听暮蝉’。我以为最好将起首一二两句移作颔联,三四两句移作起句,那对于平仄格律既不失粘,在意义上也比较自然。”
又王维《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评曰:“本诗首二句照律诗定式不尽相符,是谓用拗。倘将一二两句互易,即可合式,但意义又不对了。古人这种句法,往往不免。”
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评曰:“严沧浪谓‘唐人七律诗,当以此为第一’。但在律论律,此诗颔联竟完全是古诗句法。古人兴到笔随,偶弄狡狯,竟传诵千古,究竟不可为法。”
喻评所涉有二:一联内之对偶,两联间之粘缀。但对偶既是近体律诗的必备条件,亦为六朝诗格的普遍要求。对仗工整与否,取决于运笔技巧或工力,然亦不能惟求其工而适受其累。黄山谷云:“宁可使句不律,不可使句弱。”盖亦此意。而王维五律对偶之欠切,当可以山谷此语解之。兹不申说,只说粘缀。
说王维七律“照律诗定式不尽相符”,是指此作失粘而言,虽“一二两句互易”后其成色未免逊于原作,而就粘论粘,亦未始不合。但王维五律前两联互换之说则不敢苟同,互换后不仅中两联堆垛呆板,原诗灵动之气荡然无存,况本不失律之作,却因此而前后两半之间整体失粘。
王力认为“唐人并不把失对失粘看得这样严重”。这当是六朝二百年积淀未能尽除使然,李白“凤凰台上”、王维“渭城朝雨”,乃至中晚唐韦应物“春潮带雨”、杜牧“春风十里”仍不免失粘,均足可为证。
至喻评以为《黄鹤楼》作者“偶弄狡狯”,则恐不然。《诗薮》谓此作“歌行短章耳,太白生平不喜俳偶,崔诗适与契合”,其说不为无见,况“不复返”、“空悠悠”并不对仗。誉之为唐人七律第一,真不知何从说起。
唐子西曾以诗律“殆近法家,难以言恕”为拟:“东坡云‘敢将诗律斗深严’,余亦云‘诗律伤严近寡恩’。”其言如此,而齐梁采偶句、调平仄,亦何尝无法,惟较沈宋为宽而已。既不能无法,却不乏权变,如押韵则有“邻韵”、“进退”、“辘轳”;平仄则有“拗救”;对仗则有次联不对首联对之“偷春格”。凡此种种,指不胜屈,但尚不足以动摇粘对法之基石。这一法则在杜甫首创的一种“拗体”诗里却被打破,如《暮归》: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
此诗无一联不拗,亦无一字必救,且不避二四两字同平同仄,句尾多用三平,更不再强调粘对,读来饶有古意。此体苏黄亦间有所作,读来令人生喜。惟晚清胡朝梁辈一生屡作此体,近乎滑俗,多看则未免令人欠伸思睡。
以上皆老生常谈,一言以概之,则律诗肇始于齐梁,其平仄粘对之法定于初唐,大行于盛唐而作者于律或容有未守,至老杜而集大成,其律渐细,中晚而后则其格大备,然基于“伤严”所生发之各种变体,乃不啻法外开恩,无异在近体与永明体夹缝中辟出一片“开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