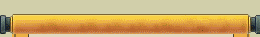
- 五律·年末吟怀(沈阳李斌老师作)
- 七律“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60周年
- 刘禹锡的诗意瑶山
- 姑苏城外寒山寺
- 律诗、永明体及其他
- 一座天姥山半部《全唐诗》
- 《全唐诗》读后感恩多
- 经典婚姻诗词
- 古今诗词名句荟萃集
- 《红楼梦》中的诗词摘录
- 皇帝雍正写的诗词
- 最美古典诗词选录
- 席慕容:写歌词比写诗难多了
- 被误译的李白诗
- 李杜相亲如兄弟
- 李杜不齐名
- 自古文人食尚雅
- 可怜身后识方干
- 这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
- 唐诗在海外
- 古人称鸡为德禽尊崇有加
- 王镛:雏凤清于老凤声
- 隋煬帝最后的日子
- “床前明月光”此床非彼床
- 诗魂悠悠,词韵淼淼
- 立夏初立,小满未满
- 千古留名的落第者
- 归有光《吴山图》记
- 趣谈文人书屋
- 文言文虚词以的用法
- 投稿:归有光的一天
- 归有光与江南经济
- 古时候的“高考落榜生”
- 对一种朴素笔触的向往
- 归有光:博学宿儒,造福一方
- “杜甫”的N种面孔
- 情诗:张静婉采莲曲
- 唐诗贬斥《后庭花》
- 芭蕉先有声
- 诗中雨中心中
- 读书人的道路选择
- 李商隐《锦瑟》新解
- 破译李商隐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空城舞罢腰支在
- 李商隐的苦与美
- 李商隐和谁“心有灵犀”
- 谈谈程序员“文人相轻”
- 戏曲里的词章之美
- 游京西古道
- 夕阳美景映古诗
- “不三不四”的由来
- 诗词曲名篇改写举隅
- 生之哀歌古今同
- 韭园村寻访马致远故居
- 欧阳修与醉翁亭
- 宋朝士大夫的外号
- 巨笔作小诗
- 宋朝对公款吃喝的治理
- 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
作者:王力老师
为着发展祖国的文化,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就必须先读懂古书。现在高等学校文科许多专业所订的教学方案中,都以“能阅读中国古籍”“能够阅读一般古籍"、“能阅读中国古典哲学文献"等,作为培养目标之一。古籍的注释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注释上的问题,牵涉的面很广,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各方面的专门知识,所以古籍的注释工作应该由各方面的专家们担负起来。在自然科学中,有关天文、数学生物学、医学等古籍,当然由自然科学家来注释;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有关文学、史学、哲学的古籍,也应该由文学专家、史学专家、哲学专家来注释。但是其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必须正确地了解古人的语言,我们所作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否则即使把句子讲通了,也可能只是注释人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古人的原意。因此,训诂学的重要性,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训诂学是中国很古老的一门学问。前人把“小学”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门,而训诂一门则以讲述故训为目的。训诂一类的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搜集和保存“故训",很少参加作者的意见。到了清代,训诂学稍稍超出了故训的范围,也就是注意到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之间的联系。按照现代的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是语文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从语言角度去研究古典文献的。
训诂学有它的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清代有些学者不甘心墨守训诂学的成规,从古音通假等方面对古籍进行研究,获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但也引起了不少的流弊。自从胡适提出了“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实用主义观点,许多人受了他的影响,抛弃了清代学者朴学的优点,而在前人主观臆测的缺点上变本加厉,以达到实用主义的目的。于是大禹变成了一条虫,墨子变成了印度人!训诂学上的实用主义,至今没有受到应得的批判。在这一篇文章里,不可能全面地讨论训诂学上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专门批判训诂学中的实用主义,只是把我最近在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感想,随便提出来谈谈。我觉得,古籍中的注释虽然是零碎的,但是也往往表现着注释家的学术观点特别是治学方法。所以值得提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来讨论。
新颖可喜还是切合语言事实
从前常常听见说某人对某一句古书的解释是新颖可喜的。其实如果不能切合语言事实,只是追求新颖可喜的见解,那就缺乏科学性,“新颖"不但不可喜,而且是值得批评的了。当然每一位持“新颖可喜”的见解的注释家,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不根据语言事实,而是凭空臆测的,但是他们的根据是那样站不住脚,甚至仅仅是语音的偶合,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了。
举例来说,《诗经》里面有许多难懂的句子。从前的经学家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对《诗经》进行了歪曲,连句子也加以曲解。现在这种歪曲可以说是已经被廓清了,再也没有人相信《关雎》是颂扬后妃之德,《柏舟》(《鄘风》)是颂扬寡妇守节的诗了。但是,虽然破得相当彻底,立起来还有困难。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诗经》的学者们住往着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叠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
《诗经》以外,对别的古书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假定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我们试把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可能这十种意见都是新颖可喜的,但是不可能全是正确的。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但是也可能十种解释全是错误的,因为都是先假设了一种新颖可喜的解释,然后再乞灵于“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那末,这些假设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了。
就一般情况说,这些新颖可喜的解释往往得不到普遍承认,聚讼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时候也有相反的情况,由于某一位学者的声望较高,他的新说得到了学术界多数人同意,差不多成为定论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好事。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简单地要求学术界对某一个问题赶快作出结论。如果在训诂学上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所谓定论也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从思想上去体会还是从语言上去说明
语言是代表思想的。我们读古人的书,必须很好地体会古人的思想。但是,当我们阅读一本古书的时候,是应该先体会古人的思想呢,还是应该先弄懂古人的语言呢?这个先后的分别非常重要,这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书面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后一种做法有陷于主观臆测的危险。有人说,现在研究老子的人,如果他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他所注释的《老子》就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老子;如果他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的,他所注释的《老子》就变成了唯心主义的老子。这句话也有几分道理。一般人把某些想当然的解释说成是“断章取义",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什么“断章取义”,而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古人的语言,使它为自己的观点服务。这样,即使把古书“讲通”了,也不过是现代学者自己的意思罢了。
上面就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的。至于就文章的逻辑性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就一篇文章来说,前后的思想有没有它的连贯性呢?连贯性肯定是有的。但是连贯性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你猜想应该是这样连贯的,古人也可能是那样连贯的。脱离了语言的正确了解而去体会文章思想的连贯性,就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总之,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该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如果先主观地肯定了古人应该说什么,就会想尽各种方法把语言了解为表达了那种思想,这有牵强附会的危险;如果先细心地看清了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再来体会他的思想,这个程序就是比较科学的。所得的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
“并存"和“亦通”
人们在注释古书中某些难懂的字句的时候,往往引用了两家的说法,再加上一句“今并存之”,或“此说亦通”。我们可以把这些情况称为“并存论”和“亦通论”。
并存论显然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注释家不愿意表示自己的意见,所以并存两说,以供读者参考。有些“集解”、“集释”、"集注”之类,也是罗列各家的解释,自己不置可否。这种做法,如果读者对象是一些专家们,那是未可厚非的,因为罗列了材料也是一种贡献;如果对象是一般读者,这种客观主义态度是值得批评的,因为两说不可能都是对的,注释家应该拿出自己的意见来,即使是不十分肯定的意见,表示一点倾向性也好。注释家总比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高些,有责任把读者引导到比较正确的路上去。
最糟糕的是“亦通论”,这等于说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随便选择哪一种解释都讲得通。这就引起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所要求知道的是古人应该说什么呢,还是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呢?如果是前者,那末不但可以“并存",而且可以“亦通",因为两种解释可能并不矛盾,在思想内容上都说得过去;如果是后者,那末,“亦通论”就是绝对荒谬的,因为古人实际上说出了的话不可能有两可的意义。
真理只有一个:甲说是则乙说必非,乙说是则甲说必非。注释家如朱熹等,他们可以采用“亦通"的说法,因为理学家的目的只在阐明道理,只要不违反他们的道理,都可以承认它“亦通”。我们如果要求知道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那就必须从两种不同的解释当中作出选择,或者是从训诂学观点另作解释,决不能模棱两可,再说什么“并存”和“亦通"了。
语言的社会性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所制约着的。远在两千多年以前,荀子就说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正名篇》)任何个人都不能创造语言。如果作家用一个词,用的不是社会一般所接受的意义,读者就看不懂,语言在这里就失掉它的作用。
固然,在语言中也有新词新义的形成,我们也承认语言巨匠们能创造新词,但是,那也不是偶然的。第一,必须有旧的词根(或词素)作为新词的基础;第二,必须为社会群众所接受,让它进入全民词汇的仓库里。因此,即使是新词新义,也必然是具有社会性。如果某词只在一部书中具有某种意义,同时代的其他的书并不使用这种意义,那末这种意义是可怀疑的。如果某一作家多次使用这个词义,虽然别的作家不用它,还可以设想是方言的关系。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在这一处讲得通,不但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连在同一部书里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末,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作家使用这种在社会上不通行的词义,只能导致读者的不了解,为什么不用一个能为社会所接受的词呢?实际上,作家并没有使用这个词义,而只是注释家误解罢了。
举例来说,《左传》庄公十年所载《曹刿论战》有这样一段话:“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有一部书把“间”字解释为“补充或纠正①”。这种解释也许是讲得通的。但是上文说过,问题不在于是否讲得通,而在于是否合乎语言事实。《左传》用“间”字共八十一处,其他八十处都不当“补充、纠正”讲,除《左传》外其他先秦两汉的古书的“间”字也不当“补充、纠正”讲,左丘明在这里不可能忽然为“间”字创造一个新义,因为这样的“创造"谁也不会看得懂。作为一个原则,注释家不会反对语言的社会性。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释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原则。
① 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想批评某一位注释家,也不是批评某一部书(一二处错误也不一定就降低了全书的价值)。举例都是顺手拈来的,所以不必注明出处。
词义是不是由上下文决定的
法国语言学家房特里耶斯说过:“确定词的价值的,是上下文。"①这句话我们是可以同意的,因为他在下文接着说:“尽管词可能在意义上有各种变态,但是上下文给予该词独一无二的价值;尽管词在人的记忆中积累了一切过去的表象,但是上下文使它摆脱了这些过去的表象而为它创造一个现在的价值。”②
一词多义,这是词汇中的普遍现象。所谓一词多义,是指它在词典中的价值说的;到了一定的上下文里,一个词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词义是由上下文确定的。岂但多义词,即使是独义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的词义也会产生不同的色调。我们不能否认:词在上下文中,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明确的价值。但是跨过真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如果认为词到了一定的上下文中才临时产生一种意义来适应上下文,那就不对了。
一词多义,无论多到什么程度,绝不能认为词无定义。何况所谓多义词也不会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杂乱无章。大家知道,多义词一般总有一个基本意义,其他意义都从这个基本意义引申出来,而且在同一时代不会有太多的意义。实词如此,虚词也如此。例如杨树达的《词诠》在“于”字下面罗列了二十个意义,那是用现代汉语去翻译后所得的幻象,实际上是不会这样复杂的。更重要的是:一个词即使有很多的意义,我们也不能说,词在独立时没有某种意义,到了一定的上下文里却能生出这种意义来。
仍以“间”字为例。依《说文》,“间"本作“閒"。“閒”字的基本意义是间隙,其他意义(除假借义外)都是由这个基本意义引申出来的。段玉裁说得好:“閒者,隙之可寻者也,故曰閒厕,曰閒迭,曰閒隔,曰閒谍。"③《左传·曹刿论战》“又何间焉”的“间",其实就是“间厕"的“间”。杜预注:“间,犹与也。”《经典释文》:"间,间厕之间。”孔颖达疏:“间谓闻杂,言不应间杂其中而为之谋,故云‘间犹与也。’”杜注所谓“与”就是“参与”,“参与”实际上是“厕身其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了《左传》这一篇文章④,选集的注释说:“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⑤这个注释跟上文所引那个注释(解作"补充或纠正")比较,真是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就原词的意义本身作出注解的,是正确的;一个是简单地让上下文来“决定”词义的,是错误的。
古人望文生义的情况较少,因为他们一般总是遵守故训的;近人望文生义的情况较多,甚至在字典辞书中也在所不免。例如《辞海》“摧”字下有一个意义是:”犹悲也。司马光诗:‘空使寸心摧。’”其实“寸心摧"的“摧”也就是”摧折"的比喻用法,不应该另立一个意义。否则就使青年人误人迷途了。
总之,我们只应该让上下文来确定一个多义词的词义,不应该让上文来临时“决定”词义。前者可以叫做“因文定义",后者则是望文生义。二者是大不相同的。因文定义是此词本有此义,我们不但在这个地方遇着它,而且在别的许多地方也经常遇着它。例如“间”字解为“间厕",不但在《左传·曹刿论战》中讲得通,在别的许多地方也都讲得通,这就合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至于望文生义,那是此词本无此义,只是从上下文推测它有这个意义,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遇着它,在别的地方再也遇不着它。例如“间"字解为“补充”或“纠正”,只在《左传·曹刿论战》这一个地方似乎讲得通,在别的地方这个意义全用不上,这就不合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这种解释是错误的。
因文定义比较有客观标准,各家注释容易趋于一致;望文生义则各逞臆说,可以弄到“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因文定义和望文生义是学术观点方法上的分歧。要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就要有训诂学的修养。
①② 房德里耶斯:《语言论》,法文本,页211。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閒”字条。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页197~198
⑤ 同上,页235
僻义和常义
人们在读古书遇见难懂的字句时,一般总是查字典来解决。人们查字典,看见了一个字有许多意义,往往有下列两种情况:不是不知所从,就是主观地选择一个自己认为适合于这一段上下文的词义。不知所从自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胡乱选择一个词义也不见得妥当,有时候反而引起误解。
注释家们查字典,和一般人不同。他们可能查《说文》、《尔雅》、《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群经平议》、《经籍籑诂》等(有些已经超出了字典的范围)。但是,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训诂学的修养,就会不知所从,或者是主观地选择一个自己认为适合于这个上下文的词义,而其实是错误的。
这里关系到僻义和常义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语言的社会性的问题。
从语言的社会性来看,语言的词汇所表达的,应该都是经常的意义,而不是偏僻的意义。一句话中用了僻词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思想的交流,妨碍了交际;如果僻词僻义用得多了,就变成不可懂的语言,失掉语言的作用了。那末,为什么语言中还存在着一些僻词僻义呢?除了方言和行业语之外,主要是那些过时了的词和意义还残存在语言里,或者在不自由的组合中出现,或者在仿古主义者的笔下出现。这种僻词僻义在语言中毕竟占极少数,如果拿它们来和常用的词义等量齐观,那就是错误的。假定一个词有十个意义(严格说起来不会那么多),在同一时代和同一语言区域中,只有少数意义是常用的意义,其他就都是僻义,其中有些僻义还是不大可信的。我们在注释一句古书的时候,除非有了绝对可靠的证据,否则宁可依照常义,不可依照僻义。依照僻义,曲解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连僻义也谈不上。那就是:字书中虽然说某词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古人的著作中无从证实。例如《说文》:“殿,击声也。”又如《广雅·释言》:“都,救也。”根据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不相信字书。
关于古音通假
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这是注释家的大忌。但是,古音通假说恰恰是穿凿附会者的防空洞。有些注释家以古音通假的理论为护符,往往陷于穿凿附会而不自觉,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古音通假说的广泛应用,开始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引之说:"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恰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尽者,迄今考之文义,参之古音,犹得更而正之,以求一心之安,而补前人之阙。”①这一个学说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摆脱了文字形体的束缚,把语音跟词义直接联系起来。这样做,实际上是纠正了前人把文字看成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唯心主义观点。王氏父子的成绩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王氏父子治学是谨严的。事实上他们不是简单地把两个声同或声近的字摆在一起,硬说它们相通,而是:(一)引了不少的证据;(二)举了不少的例子。这样就合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当然在王氏父子的著作中也颇多可议之处,那些地方往往就是证据不足,例子太少。所以说服力就不强。后人没有学习他们的谨严,却学会了他们的“以意逆之”,这就是弃其精华,取其槽粕,变了王氏父子的罪人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必须先弄清楚古音通假的性质。朱骏声说:“假借滥于秦火,传写杂而失真。”②所谓假借或古音通假,说穿了就是古人写别字③。别字有形近而误的,有声近而误的。正如现代人所写的别字一样,形近而误的别字较少,声近而误的别字较多。但是,无论如何,写别字总是特殊情况,我们不能设想古书上有大量的别字。再说,正如现代人所写的别字一样,所谓声近而误,必须是同音字,至少是读音十分近似的字,然后产生别字;如果仅仅是叠韵,而声母相差较远,或者仅仅是双声,而韵母相差较远,就不可能产生别字。例如北京人把“驱使"写成“趋使",“绝对”写成“决对",上海人和广州人就不会写这一类的别字,因为它们在上海话和广州话里仅仅是叠韵,而声母相差较远。又如上海人把“过问”写成“顾问",把“陆续"写成“络续",北京人就不会写这一类的别字,因为它们在北京话里仅仅是双声,而韵母相差较远。因此,同音字的假借是比较可信的;读音十分相近(或者是既双声又叠韵,或者是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叠韵字,或者是韵母相近的双音字)的假借也还是可能的,因为可能有方言的关系;至于声母发音部位很远的叠韵字与韵母发音部位很远的双声字,则应该是不可能的。
而谈古音通假的学者们却往往喜欢把古音通假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的双声叠韵,这样就让穿凿附会的人有广阔的天地,能够左右逢源,随心所欲。双声叠韵(包括准双声,准叠韵)的机会是很多的,字与字之间常常有这样那样的瓜葛,只要注释家灵机一动,大胆假设一下,很容易就能攀上关系。曾经有人认为杨朱就是庄周,因为“庄”“杨”叠韵,“周"“朱"双声;这样滥用古音通假,不难把鸡说成狗,把红说成黄,因为“鸡”“狗”双声,“红”“黄"双声;又不难把松说成桐,把旦说成晚,因为“松”“桐"叠韵,“旦”“晚”叠韵。这好像是笑话,其实古音通假的误解和滥用害处很大,如果变本加厉,非到这个地步不止。在语音学知识比较不普遍的时代,双声叠韵的现象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似乎一讲古音通假,就能令人深信不疑。现在我们知道,单凭双声叠韵,并不能在训诂学上说明什么问题。现在是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两个字完全同音,或者声音十分相近,古音通假的可能性虽然大,但是仍旧不可以滥用。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其他例子,古音通假的解释仍然有穿凿附会的危险。例如俞樾解释《诗·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以为“廛”同“缠",“億"同“繶",“囷"同“稛",都是“束”的意思④。
由于他这一说新颖可喜,许多注释家都采用了它。但是,为什么诗人这样爱写别字呢?为什么这样巧,在同样的位置,一连写了三个别字呢?像“億"字这样普通的数目字,为什么忽然变了一个僻词(繶),用了一个“僻义"(束)呢?《诗经》里一共有六个地方用了“億"字,其余五个地方的“億"字都不当“束"讲,其他先秦各书的“億"字也都不当“束"讲,《伐檀》的“億”字偏要当“束"讲,语言的社会性何在呢?何况“億"字用来形容禾黍之多,是《诗经》的习惯用法,《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億及秭。”《诗·小雅·楚茨》:“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億。"难道这些地方的“億"字也都能解作“束”吗?“廛”之通"缠",“囷”之通“稛",也没有什么证据。
依我看,《伐檀>》篇中的“廛、億、囷",毛传、郑笺、孔疏都讲得很对。关于“廛",毛传说:“一夫之居曰廛。”关于“億",毛传说:“万万曰億”;郑笺说:“十万曰億,禾秉之数。”(郑笺较妥。)关于“囷",毛传说:“圆者为囷";孔疏说:“方者为仓,故圆者为囷"。我们试拿上面所举《周颂·丰年》的“亦有高廩,万億及秭”和《小雅·楚茨》“我仓既盈,我庾维億"来跟《伐檀》比较,可见“億"就是十万个禾秉,“囷”就是仓廪之类,没有什么讲不通的。“廛、億、囷”都当量词用,并不像俞樾所说的“义亦不伦”。既然甚言其多,不妨夸张一些,俞氏所谓“三百夫之田其数太多”也不能成为理由。总之,关于这三个字的解释,实在用不着翻案。
古音通假说的优点和缺点既如上所述,我们就应该正确地运用古音通假而防止它的流弊。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二,“经文假借”条。
②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叙》。
③ 如果像《说文》所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那种假借不是写别字。这里指的假借乃是朱骏声所谓假借。朱氏说:“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那就是写别字了。王引之所谓:“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那也是写别字。
④ 俞樾:《群经平议》卷九。
偷换概念
滥用古音通假的学者们并不是公然抛弃故训的;相反地,他们也常常引用古训,然后牵合他们所要说明的词义。这样就从中偷换了概念。古代学者(包括清人在内)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常常陷于偷换概念而不自觉;现在我们如果再蹈这覆辙,那就不应该了。
仍以“繶”字为例。《说文》没有“繶”字。《周礼·屦人》注:“繶,缝中紃也。”“紃”就是“絛”,所以《广雅·释器》说:“繶,絛也。”胡培翚说:“繶本以紃饰屦缝之名。”繶是一种饰屦缝的丝绳,人们绝不会把这种丝绳去捆束禾黍!固然,《广雅·释诂》也说:“繶,束也",但是我在上文说过,字典所说的词义,如果没有作品来证实,就不一定是可靠的。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在这个地方也讲不清楚。他只好牵合着说:“疏云:‘谓牙底相接之缝,缀絛于其中',亦系束之义也。”从“絛”牵合到“束”,这是愉换了一次概念,而俞樾从动词的“束"牵合到量词的“束",这是再一次愉换概念。关于“缠"字也有类似的情况:“缠”字虽然可以解作“束",那只是个动词,它从来不作为量词来用的。
再以“抈”字为例。《诗·小雅·节南山》:“乱靡有定,式月斯生。”“式月斯生”这句话很难懂。郑玄说:“式,用也。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俞樾认为:“用月此生,甚为不辞”,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他自已提出的解释就不一定对了。他以为“月”是“抈"之省(其实也是古音通假)。《说文》:“抈,折也。”“式抈斯生”就是“用折此生”。俞氏再补充说:“盖乱靡有定,故民不得遂其生,而夭折也。”其实"抈”字只有具体的“折断”的意义,没有抽象的“夭折”的意义,由“折断”牵合到“夭折”,也是偷换了概念。
偷换概念不限于古音通假;凡是一词多义的地方,都可以偷换概念。何况《尔雅》《广雅》一类的书只把故训罗列在一起,并非定义式的解释,我们在利用这些书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偷换了概念。例如《广雅·释诂》:"翫(玩)、俗,習也。”“翫”与“習”是同义词,“俗”与“習”是同义词,但“翫”与“俗”不是同义词,因为“習”是多义词,兼有“狎习”和“习俗”等义,如果把“翫”字解作“习俗”的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
《说文》家们偷换概念的情况较少,但是有时候为了维护许慎的说解,也难免偷换概念。例如上文所举,《说文》:“殿,击声也。”段玉裁比较谨严,老实地说:“此字本义未见。”桂馥说:“击声者,所谓'呵殿'也";王筠说:“所谓“呵殿'者,与此义略近。”这是从“声”的意义偷换概念。朱骏声说:“击声也。……急就篇:‘盗贼系囚榜笞臀',以‘臀'为之。”这是从“击”的意义偷换概念。其实“呵殿”是中古的熟语,不能用来说明上古;而且“呵殿”是“呵于前面殿于后”的意思,跟“击声”的意义搭配不上。至于《急就篇》“榜笞臀”的“臀",那大概是“打屁股”的意思,从“击声”牵合到“打屁股”,距离也未免太远了!
《吕氏春秋·察传》说:“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偷换概念的情况也是跟《吕氏春秋》所说的情况相仿佛:换了一两次概念以后,往往面目全非!
偷换概念是望文生义的自然结果。望文生义的人们不会毫无根据地“生”出一个“义"来,而往往是引经据典,然后暗渡陈仓,以达到他们所想要生的义。如果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偷换概念的毛病就不会产生了。
重视故训
古代的经生们抱残守缺,墨守故训,这是一个缺点。但是我们只是不要墨守故训,却不可以一般地否定故训。训诂学的主要价值,正是在于把故训传授下来。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所说的故训往往是口口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汉儒读先秦古籍,就时间的距离说,略等于我们读宋代的古文。我们现代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还是千年后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大家都会肯定是前者。因此,我们应该相信汉代的人对先秦古籍的语言比我们懂得多些,至少不会把后代产生的意义加在先秦的词汇上。甚至唐宋人的注疏,一般地说,也是比较可靠的,最好是不要轻易去做翻案文章。
当然这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翻案。今天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又有了晚近出土和最新出土的古文字和古代文物,而且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得书较易,我们在这些方面比古人具备更有利的条件。再者,经生们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捏造了一些“章旨",跟着就有意识地歪曲了一些词义。还有所谓声训,绝大部分都是不科学的。这些都应该彻底批判,而不能有丝毫调和。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地去了解古人的作品,不是主观地把它说成什么样子,而是根据语言事实,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怎样对待疑难的字句
注释家对待疑难的字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不懂就承认不懂,这就是一般所谓存疑;第二种是虽然不懂,也勉强注它一注,以为不注就没有尽注释家的责任,有时候还抛弃故训,另立新说,而以古音通假之类的方法来证明。我赞成第一种态度。
大家知道,古籍在传写中产生的错误是相当多的。校勘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用校勘不同版本的方法来订正传写中(后来是印刷中)的错误。假如没有不同版本,即使有脱文,衍文,误字和错简,都无从知道。即使有了不同版本,也有可能是以讹传讹。我们还不可能把一切脱文、衍文、误字和错简都订正过来。在有疑难问题的字句中,正是脱文、衍文、误字和错简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按照抄错了(或刻错了)的字句强加解释,那就真是痴人说梦;假使古人有知,他们一定会窃笑我们了。
存疑并不是不可知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科学的态度。今天的存疑,可以为后人进一步研究问题提供参考;将来有了新的材料或者是新的发现,问题仍旧是可以解决的。当然,遇着有疑难问题的字句,首先是尽可能要求解决,没有深入考察而马上“存疑”,那种懒汉作风也是不对的。
以上所论,主要是针对上古的书籍的注释工作来说,因为所谓训诂学,一向被认为经学的附庸,传统的训诂学正是为了解上古的典籍服务的。至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那自然可以适用于一切注释工作。这篇文章涉及的方面太广,许多地方谈得不够透彻;有些地方跟我的旧作《新训诂学》和《双声叠韵的应用及其流弊》可以互相阐明。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1月号;
又《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王力文集》第19卷
- 本姓解第三十九
- 赠李明府
- 送常侍舒公归觐
- 兰溪(在蕲州西)
- 徐淑简介
- 小诗有味似连珠
- 贺新郎(戊戌寿张
- 寄上礼部李侍郎
- 送客赴洪州(一作
- 夏日江寺寄无上人
- 风入松_心心念念
- 怨情
- 塞下曲_边头能走
- 瑞龙吟(寿吴丞相
- 华清宫和杜舍人(
- 观叶生画花
- 柳梢青_子规啼月
- 草_草,草。折
- 上翰林丁学士
- 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 点绛唇(闺思)
- 赠别冀侍御崔司议
- 薛稷简介
- 诚则明,明则诚
- 斋居春久,感事遣
- 定风波_密约偷香
- 浣溪沙(江村道中
- 赠僧二首
- 乌夜啼_绿外深深
-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
- 留宿罗源西峰寺示
- 避地越中作
- 戏赠乐天、复言(
- 早秋夜作
- 送长安罗少府
- 咏西施(一作杜光
- 偶题寄独孤使君
- 浣溪沙(时在西园
- 蜘蛛讽
- 闲居酬张起居见赠
- 须臾火尽灰亦灭
- 自怜柳塞淹戎幕
- 江上待潮观
- 西望日依依
- 交关但交假
- 俾吾为泰山之阿
- 归私暂休暇
- 骚人泛洞庭
- 喧传京国声价
- 且复穹庐拜
- 宛转回文语
- 一笑巡檐清影瘦
- 最难欢聚易离别
- 芳草年年发
- 愿随鸡犬升仙
- 谁何不敢讥
- 碧梧树老鸾飞远
- 五阴山头乘骏马
- 春茶雨后猿狙摘
- 晨鹍凄清不可闻
- 鬼谷上窈窕
- 天行已过来万福
- 西北驰使驿
- 且当勤举杯
- 身闲书漏不胜长
- 埋瓮作小潭
- 参差烟树灞陵桥
- 爰植予之中庭
- 万舻飞戈快
- 自笑与世疏
- 天乎如可恃
- 醉倒老浮丘
- 君不见杞梁之妻善
- 远分苍树绕楼台
- 客有绿林嗟路阻
- 惟恨得酒悭
- 野性登朝常蹙踖
- 设斋无限
- 归更一旬期
- 虽死不亡
需保留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gushici5.com/blog/202304/58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