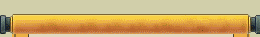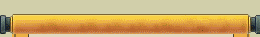折柳相别是唐诗中意味厚重的意象。《三辅黄图·桥》:“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就记载了的这一习俗。颇为奇怪的是,世人一再说灞桥折柳相别是汉代的习俗,但我们在彼时彼地的汉代文献中却并未找到相应的记录。而当时的人们对此似乎也没有丝毫的“反应”,而诉诸歌咏的大约都在隋唐以后,而且运用得颇为娴熟:“今日垂杨生左肘(王维《老将行》)”,这里垂杨即指垂柳,源于隋炀帝赐柳杨姓。写诗付诸咏唱,说明这一概念是天下的共识而不仅限于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群落。此外,还有“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李白《忆秦娥》)”、“朝朝送别泣花钿,折尽春风杨柳烟。(鱼玄机《折杨柳》)”、“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落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刘禹锡《杨柳枝》)”、“半烟半雨江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絮惹春风(郑谷《柳》)”。
《三辅黄图》一书,相传为六朝人撰写,作者姓名佚失。它是研究秦汉历史,特别是研究秦汉长安、咸阳历史地理的可贵资料。西北大学历史系陈直先生对此书作了有益的校证,并提出其为中唐以后人所作。且唐人习俗,往往将当代事以汉代之。如白居易《长恨歌》明明是写本朝事,却偏要说“汉皇重色思倾国”云云。
事实也许是,隋炀帝的地位使得柳树升格到了国家与家乡的象征符号。因而在异地相别的时候,折柳相赠便有了进而兼济天下、退而眷念乡梓的意味。隋炀帝的名声使得后世文人有意回避并挪移了折柳相赠的缘起时间。但很快,以文人认同的方式尊柳,关中民间相沿至今的民俗是孝子的拄棍为柳木棍,且最终是要插在坟头,有成活者便成为祖茔之树,仿佛国家之社树一般。
唐传奇《炀帝开河记》可能是最早提出隋炀帝赐柳树国姓的文献。“功既毕,上言于帝,决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阳迁驾大渠,诏江淮诸州,造大船五百只。龙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到大梁,又别加修饰,砌以七宝金玉之类。于是吴越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至于龙舟御楫,即每船用彩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牵之。时恐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乃牵舟之人护其阴,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时有谣言曰:‘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栽毕,帝御笔写赐垂柳姓杨,曰杨柳也。”其后明代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二十四卷、清初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四十回中又分别演绎了以上传说。
自古以来,封建帝王有赐姓于臣以示尊崇的传统。在中国,被皇家赐国姓是无上的荣耀,与皇家同宗同族,便拥有了无形的政治资本。民间传说将柳树说成“杨”姓,则将它上升到国姓的高位格局中。柳树便不再是长堤边随意栽种的树木,而是皇家的象征、国家的社树。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使人们感觉到国的象征便是家园的象征。隋炀帝赐姓的民间传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对于唐朝人来说,看到柳树便会联想到前朝的重重旧事。岁月演进,朝代更迭,前朝是唐人先祖生活的时代,先祖所居之地便是我们的祖籍。人总是念旧的,祖先的丰功伟绩、风花雪月虽都无关今日,却是整个家族不能磨灭的记忆。前尘往事随着朝代的更迭湮没无闻,先祖也相继离我们而去,只剩下那个时候栽种的柳树在风里飘摇,让我们回忆起先祖所生所处的时代。柳树便是唐人精神家园中的社树。清明插柳的习俗在唐宋时才见于文献,似乎可看作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反馈。而“杨柳”一词反复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与文本中,须知那不是联合词组,而是偏正词组的典型结构。
时代的车轮不停歇地滚动,让我们于昨日匆匆作别,柳枝成为唤起离别记忆的契机。看到柳枝随风飘舞,便会想起离开家的那一刻,父母的眷恋不舍,恋人的欲说还休,朋友的后会有期……种种思念涌上心头。此时,柳枝便成为文化符号,所指便是故园,便是桑梓,便是朝思暮想的家……折柳相赠便是这一情感的呈现与传递。于是,我们在唐人的书卷中读到了前面引述关于柳树的种种。
古人何时攀折赠别,折柳赠别,见柳思归。民间传说对精英文化也产生了影响。柳树的文化内涵得到了全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可,柳树带来的是一种归属感。诗词中反复吟诵,散文中不断意象叠加……于是,我们知道了,在文化认同方面,柳树在中国文化中已具有了“社树”的意蕴,并且代代相传。在上坟扫墓缅怀先人的节日里,将“社树”的枝条佩戴在身上,即是对死别之人的追忆,也是对部落群体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