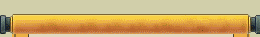本文我们来谈下清诗纪事初编的师承与渊源,诗歌之有纪事,早滥觞于《尚书》有关虞廷《赓歌》、夏《五子之歌》的记载;兹后,《左传》中有《野人歌》,《吕氏春秋》记《涂山》,《穆天子传》述《黄竹》;再如诗三百的传序、王逸《楚辞章句》题解,无不具有纪事性质。由此,中国虽然没有长篇史诗,但诗史的观念,却贯穿于整个古典诗歌的传统之中。《初编》之作,对中国诗学精神中的纪事功能有极到位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然可以认为《初编》的渊源恰出自于中国诗学的写实风格。然此点甚为笼统,因为中国最好的诗歌诗选,皆具此关心民瘼、恪守良知的共同性格;据笔者考察,邓之诚先生撰《初编》的近源,应是元好问的《中州集》、钱牧斋的《列朝诗集》、及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中州集》以诗存史、系念故国的意义,一直到明清鼎革之际方才凸现。明代末年,毛晋刊刻《中州集》,视其为野史之一。钱牧斋继承程嘉燧的遗愿,编撰《列朝诗集》,在其序言中云:“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列朝诗集》与《中州集》的关系,甚为彰然。
《雪桥诗话》撰写于民国初年,缪荃孙为其作序,谓之国朝掌故书,并言“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李详为之作跋,亦云:“本朝之事其意深厚,其旨隽永,其征文考献之心,无标榜门户之习,别裁伪体,导源正宗。其有资史料,则遗山之中州集,牧翁之列朝诗集,小长芦叟之静志居诗话,顾秀野之元诗选也。⋯⋯钱朱之选,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君书至弥其憾。”前者指出《雪桥诗话》与《中州集》可共看同论,后者则进一步表出其于《列朝诗集》的联系;职是,《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此一源流可以确定。
《雪桥诗话》自跋:“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其人足纪而无诗,其诗足纪而无事,概未之及焉。⋯⋯有未竟者,当俟续编。”与《初编》自序:“继计有功厉鹗陈田而作,僭妄之讥,知难幸免,然三家名为纪事,而诗多泛采,无事可纪。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聊符纪事之实,或者不为大雅所弃乎。”皆言其选诗的着眼点乃在于诗中所记载的史事;
《雪桥诗话》自跋:“为书十二卷,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与《初编》自序:“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是集采诗即依此为准。”皆言采诗的标准,是以诗系事;《雪桥诗话》自跋:“若夫网罗旧闻、整齐排类,为本朝一代诗史,与太鸿、秀野、蒙叟、锡鬯诸老之书相赓续,则以俟诸博雅君子。”与《初编》自序:“若钱书摹中州集,以史自命,更非所愿闻也。”皆表出文学与史学,虽血脉相通,但气质倾向究竟不同,云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固可,而言诗皆为史则未必的观念。而陈宝琛序《雪桥诗话馀集》曰:“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率以诗为经,以事为纬,其最难者,如举一人之事,每臚举他人所赠诗以证其人之生平。”评其为一代之良史,金蓉镜《雪桥诗话三集》序指其“谈诗而怀国政、念旧俗、系族世、序交游,正得论世知人之旨”,则与本文第二节所总结《初编》之主旨相合。此外,据邓嗣禹等所撰《邓之诚先生评传》一文,杨锺羲与邓之诚先生为忘年交,以杨邓之交谊,邓之诚先生自有可能受杨之影响;此外,《骨董琐记》中提到《雪桥诗话》共有五处,《初编》的小传中亦有多处直接引用《雪桥诗话》处。据此推论杨锺羲的诗学、史学思想对邓之诚先生具有一定的启发,恐非臆断。放开去看,杨锺羲的诗学思想,受晚清以来诗(词)通《春秋》思想的熏习(此点,陈三立、陈衍、沈曾植、朱古微等均有论述)。职是之故,《雪桥诗话》对《初编》之编撰有直接影响,而其要乃在于诗史相通观念之递承一节,亦可确定。
综上所述,《初编》本于对中国传统诗学求实存真之史家性格的准确把握,而其体例范式、编撰宗旨,则与《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一脉相承。自陈寅恪先生标举“诗史互证”观念以来,诗歌与史事的互发共证,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阐述。邓之诚先生师承《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诗史相通的风格,秉持“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主旨,以纪事诗编表达其“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亦可视为对“诗史互证”的另一番探求。